【书单】病毒、谣言与大数据:考察这场疫情的六个维度
一场突如其来的全国性疫情,打破了承平日久的我们的许多幻觉。
原来在城市文明已经站稳脚跟的地方,仍然有如此多的人不顾禁忌追逐野味。原来我们的公共卫生体制仍然漏洞频出,并未充分吸取17年前的教训。原来所谓的谣言并不都是负面影响,在关键时刻足以救人性命。原来17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只有一位敢于打破禁忌说真话的钟南山。
虽然“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频频被人提起,但发生过的历史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疫情时期的种种乱象,同时对照检视政府、民间在应对方面的得失。
以下六本书,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维度去考察病毒和城市化、公共卫生制度与政治、谣言与真相之间的关系。
SARS的教训

作者: [美]劳里·加勒特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作名: 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
译者: 杨岐鸣 / 杨宁
出版年: 2017-1
“非典”已经过去17年,但除了媒体报道合集、医生回忆录、英雄事迹之外,仍然没有一本足够有分量的全面反思著作,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许多错误今天重演的原因之一。虽然国人的反思远远不足,但国外关注疫病问题的记者肯定不会错过这场波及全球的传染病。
《逼近的瘟疫》虽然聚焦于20世纪后半期,记录了人类发现、研究埃博拉、拉沙热、AIDS等传染病的经过,观察了病源和传病媒介如何变化,以对付人类自我保护的防御武器。
在中文版序言中,作者对于SARS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如下分析:
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SARS促使了他们的惊醒。中国领导人看清了对流行病秘而不宣的代价,因为整个世界都不满于否认这种新疾病的存在。加拿大领导人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发现自己竟忽略了医院的传染控制措施,终使医院成了SARS的传播中心,真是令人痛惜。美国的领导人原本感到高枕无忧,深信本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确有能力保护美国民众不受微生物的威胁,如今也忽然关心起万一SARS暴发,对国家安全会有何种影响了。
这样的反思与本书的另一条主线一脉相承,那就是指导不当的医疗措施、方向错误的公共卫生政策、目光短浅的政治作为或不作为,一次次成为病毒的“帮凶”。
城市化必须迈过瘟疫这道坎

作者: 〔美〕史蒂芬·约翰逊 (Steven Johnson)
出版社: 译言·东西文库/电子工业出版社
副标题: 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
译者: 熊亭玉
出版年: 2017-1
无论是SARS还是2019-nCoV病毒,公众的普遍共识都是祸起于野味,中心城市处于卫生防疫空白地带的野生动物市场成为滋生病毒的“定时炸弹”。似乎只要顺应民意将吃野味的行为入刑,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然而,何以在现代养殖业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仍然有如此多的人甘为一口野味不惜铤而走险?这就并不是人人喊打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农业时代在城市文明中的顽强遗留,也是权力欲望冲破城市秩序的某种外化。
20年间两次波及甚广的流行病,足以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彻底拆除这些“定时炸弹”,从源头上阻断病毒的传播,这是我们真正进入都市社会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160多年前伦敦的一场瘟疫正是形塑当今城市的一股重要推动力,《死亡地图》就讲述了这背后的故事。
在此之前,伦敦是拾荒人的天下,应对250万人口聚集的城市基础设施——垃圾回收、公共卫生部门、污水处理中心等还都没有出现,粪便漫溢、污水横流、臭味熏天是伦敦人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观,也成为霍乱的温床。在当时,每隔四五年,伦敦就要爆发一次霍乱,每次爆发都要夺走上万条生命,进而波及整个英国。
霍乱因何而传播?医生约翰·斯诺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伦敦霍乱的大量病例都是发生在缺乏卫生设施的穷人区,他得到了所有因病去世的人的详细住址,并在地图上用黑杠标注死亡案例,显示出传染源是一口公共水井,霍乱中的死亡者正是围绕着水井分布和扩散。
在这份“死亡地图”面前,伦敦政府开始痛下决心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建立起了大规模的供水网,全部配备压力和过滤装置。英国的经验后来又被欧洲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复制。因为这份地图,此后伦敦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霍乱流行事件。
卫生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国进民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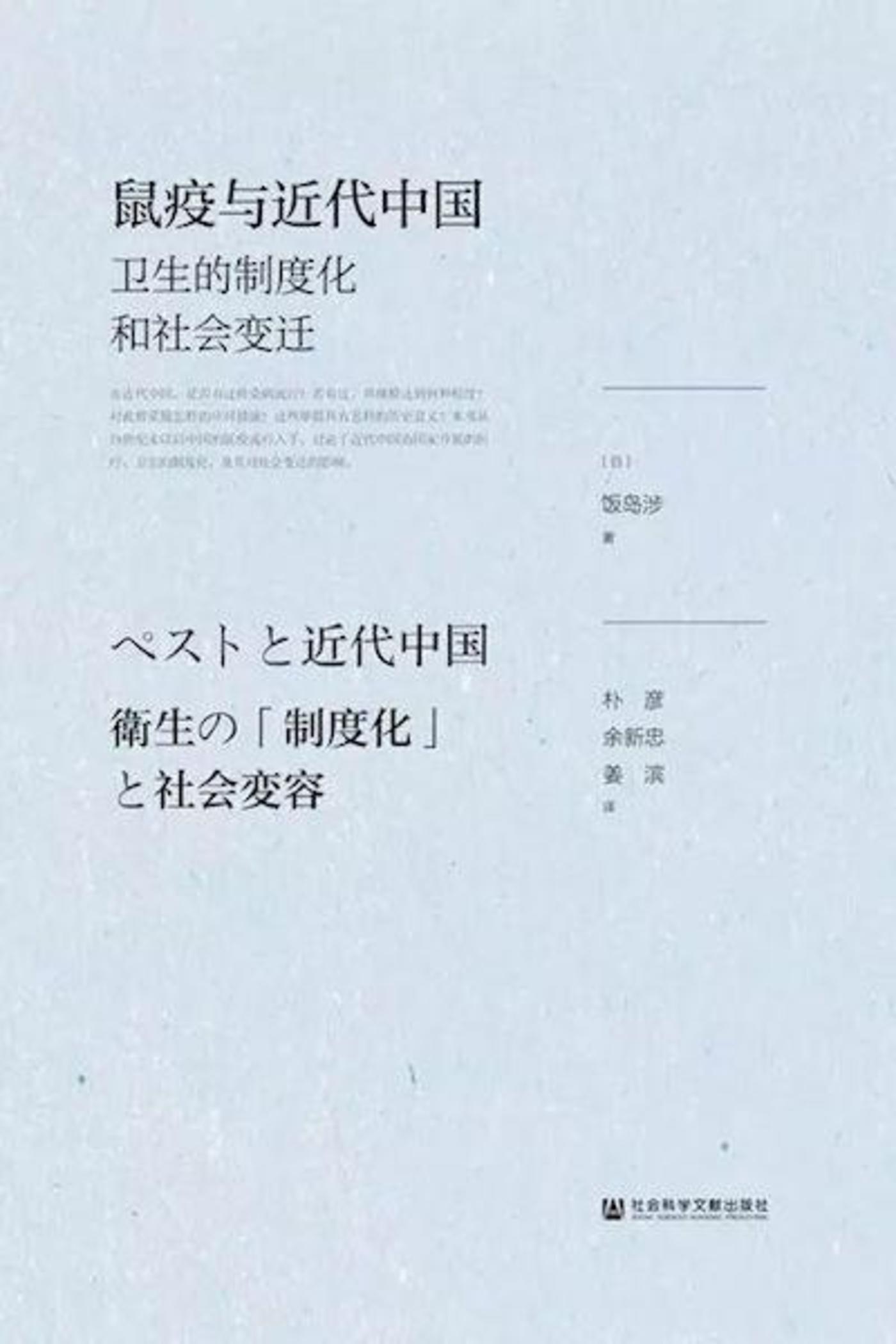
作者: (日) 饭岛涉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原作名: 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
译者: 朴彦 / 余新忠 / 姜滨
出版年: 2019-4
任何城市和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都要迈过一道道传染病的关卡,中国也不例外。《鼠疫与近代中国》就梳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卫生制度的形成,以及传染病的流行是如何重塑社会组织,促成“公共卫生”概念的。
根据作者的研究,对于19世纪末的鼠疫,清政府仍沿袭以往对瘟疫的应对办法,即命令地方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其结果是,在广州腺鼠疫流行时,担当实际防治措施的是民间团体。传染病流行时,这种由民间团体做出应对的情况,在中国社会中是极为常见之事,善堂等民间团体、乡绅、会馆、公所等对清末地域秩序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这种“政府拨款、民间实施”的模式伴随着殖民权力的介入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各种权力的角斗过程中,卫生制度和防疫检疫权最终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现代卫生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动员,使政府成功地介入社会。
实际上,卫生体系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和当时的许多事情一样,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这些配套的部门和制度,否则无法被纳入国际游戏规则。一场场自上而下的“卫生运动”并非出于公众的权利觉醒,更多的是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
这本书促使我们思考,这次疫情过后如何审视公共卫生体系中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关系,如何促使国人卫生意识的真正觉醒。
大数据能帮助我们彻底消灭病毒吗?

作者: [美] 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
原作名: The Viral Storm : the Dawn of a New Pandemic Age
译者: 沈捷
出版年: 2014-4
如果说约翰·斯诺的“死亡地图”是早期的大数据分析工具,那么在今天,无孔不入的数字监控完全有能力在疫情演变成流行病之前及时发现和应对。致力于流行病早期检测和控制的独立研究机构Global Viral创始人Nathan Wolfe,在《病毒来袭》一书中就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的流行病预测。
谷歌的工程师们通过搜索与流感相关的关键词,建立了一个预测流感趋势的系统,比美国疾控中心提供的流感数据准确率更高。2009年甲型H1N1病毒大流行期间,英国两位计算机科学家通过追踪Twitter中与流感相关信息的出现频率,并将结果与官方卫生数据比对,发现准确率达到了97%。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构想了流行病未来的末日——在疫情聚合图的帮助下。这是一张包含所有人所在位置、感染的微生物、流动的地方、接触的人,结合了数字化和生物学的信息图。在作者看来“谷歌这样的组织已经帮我们创建了一个‘环球神经系统’,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等同于‘环球免疫系统’的东西,就需要研发结合政府和非政府体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术。”
虽然作者理想中的疫情聚合图尚需时日,不过公共交通和地图应用的人口流动数据已经为这次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参考。只是高铁、航班的实名制并不能帮我们完全锁定同乘者,仍需在微博等网络平台寻人,反映出联控联防运行机制中间的“断层”。同时,打造一张巨细靡遗的疫情防控网络的同时,如何处理隐私泄露的难题也正在变得日益紧迫。
谣言不等于“虚假消息”

作者: (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世界最古老的传媒
原作名: Rumeurs: Le plus vieux media du monde
译者: 郑若麟
出版年: 2018-1
8名最早公开新型冠状病毒信息的人士12月31日因“散播谣言被查处”,疫情爆发之后却被民间追认为“八义士”,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亲自发文谈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和任何一次公共事件一样,从此次疫情发酵开始,谣言问题注定将相伴始终,尤其是在官方机构和媒体公信力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无论是一再被打脸的官方消息,不断反转的网络舆论还是到处滋生的小道消息,对于权威信源的“失信”和集体恐慌都是谣言孽生的沃土。在最高法院语焉不详的文章中,谣言在法律被认定为是对“虚假信息”的表述。当有未得到及时救助的患者在网上求救时,“造谣”的指控更是成为雨点般砸下的铁拳。
对于谣言这种民间舆论的自然产物,无论官方、民间都将其认定为仅有负面作用的贬义词。然而,这可能是某种“中国特色”。《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谣言的定义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消息”,“真实性”并不属于它的定义范畴。
谣言作为一种“街谈巷议”也不应带有贬义色彩,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或不信任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可以说,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
将谣言视为一种集体意识的表达,集体情绪的投射,通过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加以引导舒缓,而不再简单粗暴地粗暴判其为“虚假信息”,才能避免最高法院面对谣言时的自相矛盾(“不是所有的不实信息都要进行法律打击,但是在决战新型肺炎的特殊时刻,有些谣言必须严厉打击”)。
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钟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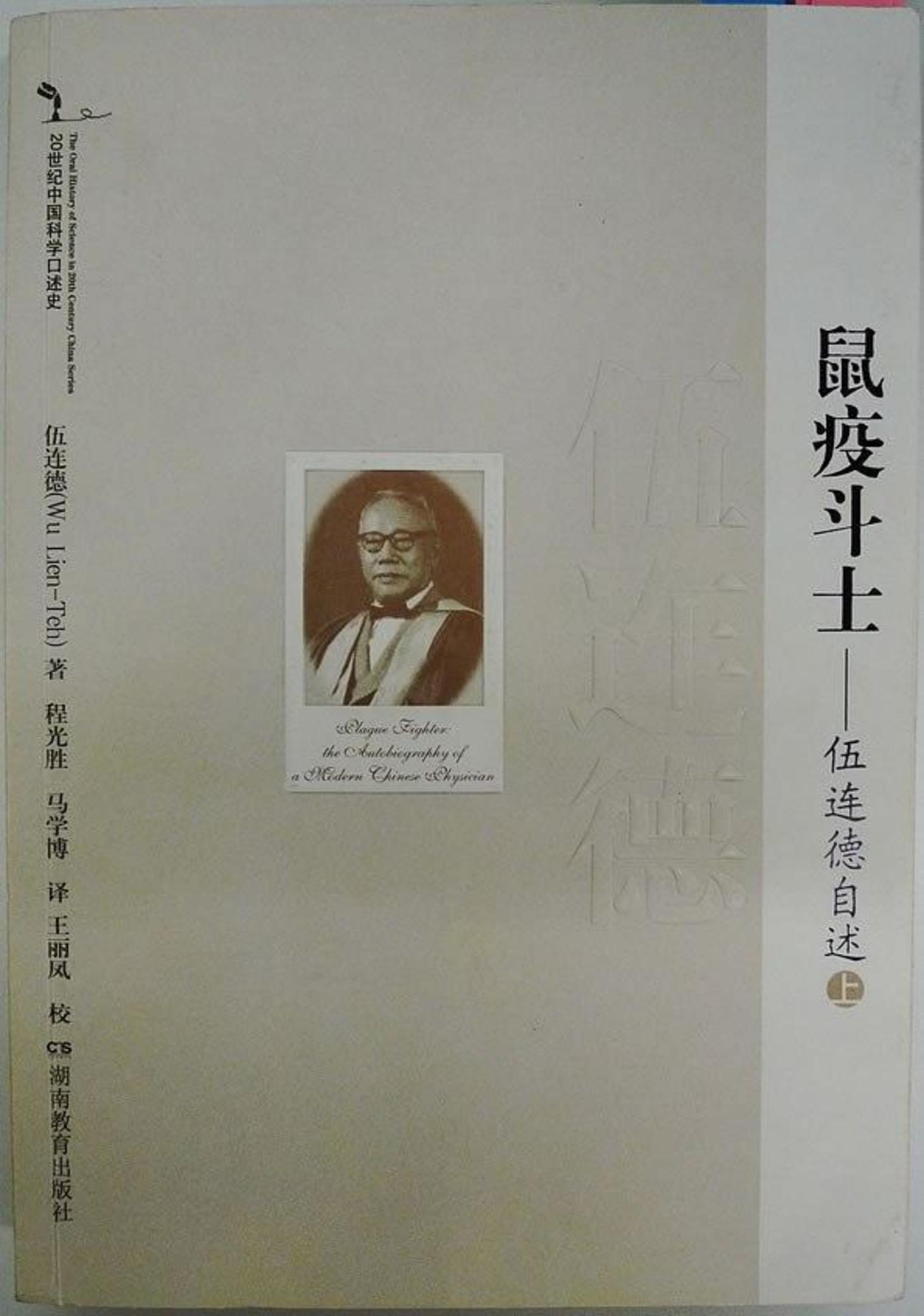
作者: 伍连德
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副标题: 伍连德自述(上)
原作名: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译者: 程光胜 / 马学博 / 王丽凤(校)
出版年: 2011-3
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毒疫情,110年前几乎以一己之力扑灭东北鼠疫的“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再次被大家提起,一篇篇十万+文章应运而生。但正如豆瓣用户@阅湖在《什么是“伍连德奇迹”》中指出的,成就这一“奇迹”的首要因素,是清末官制改革背景下、中央层面“庇护人”(patron)的绝对支持。
实际上,“庇护人”(patron)一词正是伍连德自己在其自传《鼠疫斗士》(Plague Fighter)中的说法。在这本自传的扉页上,伍连德把此书献给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在剑桥就读时的恩师William Napier Shaw爵士,另一个则是国民政府首任总理唐绍仪的侄女婿施肇基。
正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全力支持,加上地缘政治压力下东三省总督锡良对于“中央空降干部”的充分授权,才让伍连德得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打破常规,果断、灵活地推行各种防疫措施。”
1月20号,钟南山率先对媒体明确表示存在人传人,并首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打破了地方政府的信息信息封锁。这位84岁的老人17年后不得不重新出山打破僵局,和一百多年前的伍连德遥相呼应。
正如微博博主@狠狠红 所说:他不仅需要科学上的成就,还需要政治威望,需要公众话语权。你要让一个人出来敢说话,安全说话,说话能被听到,说话能管用,需要一个赋权。钟南山没有接班人的原因在这里,没有人获得赋权。钟南山获得这个赋权,已经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了。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







